
日/记者:Gary Libot
译者 /Tengjiao Tan
巴黎南大学(Paris-Sud ) 名誉教授赛尔吉·拉图什( Serge Latouche )
自1960年以来深入批判发展与经济增长。他认为从二战开始科学逐渐成为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对于技术和科学而言,这都是历史的空前。科学技术已经,也正在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前无古人又绝无仅有的角色,同时它也成为了资本主义热工业膨胀的源动力。
科学批判 — 您有很长时间作为致力于发展的经济学家,那么发展这个概念来源于哪里呢?
赛尔吉拉图什( Serge Latouche ) : 每当我 们去寻找概念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些随意。“发展 ( développement ) ”这个词是由生物进化学来的,与“增长 ( croissance ) ”有些类似。我们可以发现,很久以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德语文本中 “ entwicklung (发展、成长)”在法语与英文环境中通常被翻译为“ développement ( 发展 )”具有经济的意味。如果将前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 Harry Truman ) 1949年1月20日的著名演讲作为“发展”这个概念诞生的标志性日期,那是因为它抛出了一个有力的符号,那就是经济“发达 (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与“欠发达 ( sous-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
“ ‘发展 ( développement ) ’和‘增长 ( croissance ) ’这个词一样,都属于生物进化学。”
很久以前世界被分为五个大陆,上面生存着数百个国家并拥有它们各自的习俗。 当然也就存在着“原始的”与“野蛮的”以及另一些“文明的”。但这些类别模糊不清。 西方国家并不知道把谁放在这些类别以及另一些类别中。中国和印度是开化的吗? 如果说非洲人是原始的,那么南非有应该被如何认知?这样的问题有很多。在如何分类国家方面,规则大都十分模糊并且存在着严重主观性。
1949年,由于两个最大的帝国——英国和法国使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具威力的霸权主义国家。因为其经济发展最为蓬勃,美国虽然不一定是最文明或最有文化的,却可以拥有制定一个新的国家分类标准的权力,以及强迫所有人接受一个共通的观念——富有与否即发展与否。这种划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方式,将人类的机体及社会一点点视为并必然化为自然进化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沃尔特·惠特曼 ( Walt Whitman Rostow ) 的《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主义宣言 (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 》(剑桥大学出版社1960年发行),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的概念。这标志着文明与野蛮对立的结束,同样也标志着我们可以凭借经济判断我们是否处于一个传统社会、变迁中的社会、成熟社会等等。当然,与之相对的所有生物都存在的衰落阶段将不复存在。总是不断的在增长,这是一种伴随着意识形态简化为纯粹的经济语言的演化。
“ 我们认为经济是一种有机体,这是一种欺骗。经济只可以作为一个部分而并不是整体。”
美国人赢得了战争,因为他们拥有最发达的技术。对于其他人来说能够将技术转移给他们就足够了。这就是联合国所谓的“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的援助的开始。与此同时美国能够抢占前殖民地国家的市场。必须要重申的是:美国正是极大的从前殖民地独立收益的国家。当然也尤其是出于这个原因,美国也没有进入共产主义轨道。因此杜鲁门所说的发展不过是生物学领域的发展概念在经济领域的迁移。对于查尔斯·达尔文来说,增长是生物体的数量转化;发展是质的转变。因此我们将经济视为有机体是一种欺骗,因为经济是一个部分,而不是整体。
科学在经济发展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这是一个核心问题。但是应该明确的是:在热工业革命的初期,技术并不来自科学家,而来自工匠。无论是詹姆斯·瓦特( James Watt ) 发明的蒸汽机;还是约翰·凯( John Kay ) 改进的织机,都不是科学家的成果,而属于工匠的成果!他们是天资卓越的工匠,他们甚至没有受过正经的教育。法国大革命中将安托万·拉瓦锡( Antoine Lavoisier ) 斩首也并不是偶然,因为共和国不需要化学家。甚至1914年,法国领导人还将化学家派往前线,直到德国人使用了芥子气。这时我们发现了科学在战争中的具体应用。这些化学家被立即召回实验室工作:去研发化学武器。
“ 从经济发展这个概念浮出水面的时代起,我们开始谈论技术。我们谈论它比科学要多,它将在发展中起支撑作用。”
直到二十世纪科学在发展中都没有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1940年代开始“经济发展”这个概念被提出的那一刻起,“科学技术”就被人经常谈及了。它们的诞生可以追溯到曼哈顿计划。这些“科学技术”扮演着“发展”的核心角色。但是必须要知道的是,它们与“科学”有很多不同之处。当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提出了相对论时,他是一位科学家而非技术员。当时他是瑞士伯尔尼联邦知识产权研究所 ( l’Institut Fédéral de la Propiété Intellectuelle а Berne ) 的图书管理员,他仅仅做着一些纸面工作。正是这些工作让他能够提出那些前无古人的理论。这与1950年代乃至今天的“科学实验室”没有任何关系。
通过“曼哈顿计划” ( Manhattan Project ) 这项卓越的技术科学项目,技术人员与科学家合作。与此同时技术员成为科学家,科学家成为技术员。在此之前,科学家们只能在贫穷的状态下工作。但在这个时代,曼哈顿计划带来了技术进步和巨量的金钱。今天的美国,每个研究实验室都会拥有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设备。“科学技术”,而不是“科学”在发展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质疑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学的利用”是必要的吗?在您看来我们的社会应当如何转变,以及重新获得界限感呢?
我相信我们需要使科学非殖民化,西方的科学应当回到伽利略 ( Galilée ) 以前。那样的话自然将会更多元;会更加服从数学原理。当然数学确实是一门抽象科学,一种令人生畏的结构,自然并不服从这个数学现实。
“ 经济学家已经搞砸了,他们以牛顿的理性力学为基础,建起他们的规则。而经济生活遵循着热力学原理,尤其是熵增定律。”
这就是为什么说经济学家已经搞砸了,他们以牛顿的理性力学为基础建立起他们的规则。而经济生活遵循着热力学原理,尤其是熵增定律。有一些不可逆的自然法则在数学中并不存在。而古典经济学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
科学认为,人类在可以做的事情的可能性上没有限制,这被称为“普罗米修斯的科学 ( la science prométheene ) ”他认为人就像造物主。这种科学需要被修正。另一些些科学观念就当然拥有一些理想的智识,和科学的好奇心,它们并没有被权力的意志所吞噬,只是被我们观念的特性所吞噬。
除了协助和陪伴经济的发展,科学是不是能够帮助限制经济的发展?
是的。自从科学家成为科技和经济的巨型机器的公务员开始,科学就开始在发展中扮演驱动角色。只要科学家是独立的,他们就不会去关心那些所谓的什么发展。我可以想象公元前三世纪在耶稣之前,亚历山大人 ( Alexandrins ) 的科学。他们开发了所谓的安提基色拉 ( la machine d’Anticythère ) 机器。这台机器于20世纪初被发现,科学家们对这台机器的精密性感到惊讶。他被认为是第一个古代计算机。它可以被用于计算恒星及行星的位置。这台机器是这些人能拥有重要技术及能力的证据。但他们仅仅用这台机器制造一些装置和自动装备。他们的技术能力和科学知识脱离了应用和生产。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热工业革命,当时工匠们无法解决一些技术问题,他们呼唤了学者们,而后一场对话展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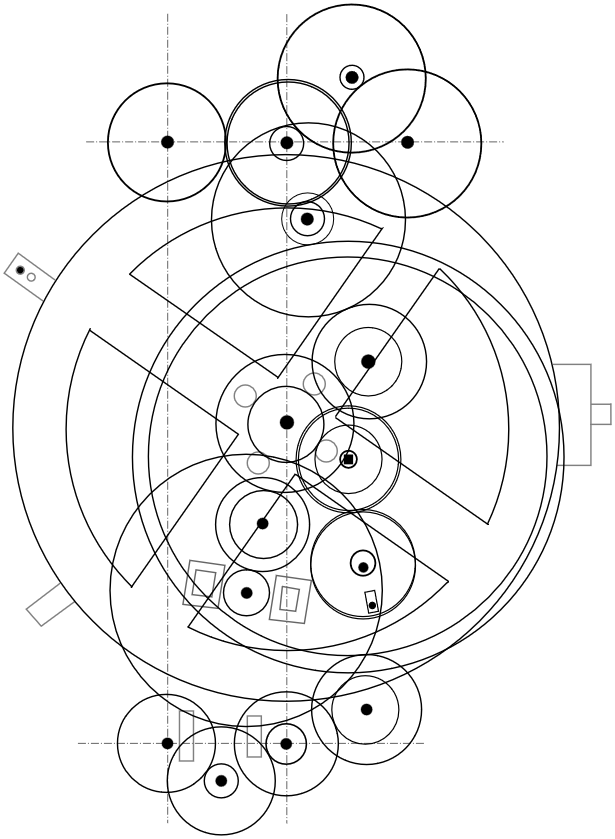
仅仅是在二战以后科学家就成为了技术员。工作上的物质需要让他们一点点失去了自由,他们逐渐成为了靠薪水为生的人。研究人员对私营部门的依赖性逐渐严重起来。这导致了今天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在健康领域,很少有科学家研究内分泌干扰物,因为药学实验室对这些研究不感兴趣,这些研究的影响力通常属于基因研究。农业的情况也是这样,在农业生态学和土壤生命学方面,几乎没有关于肥料和杀虫剂的有影响力的研究。 一个根本问题是:科学倾向于向市场和资本推销自己。
国家、市场、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是什么?
本源上来讲发展是国家的事务,市场并不是获得它的工具。发展是一种形式的战争。对伊万·伊利希 ( Ivan Illich ) 来说,这是一场针对穷人的战争。就像雅克·奥斯特 ( Jacques Austruy )——《发展丑闻》的作者在1987年解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解放”的社会没有发展的愿望,他们有反对饥荒的愿望和过上更好生活的愿望,但这些愿望不是对发展的渴望。
“ 从一开始,只有国家可以为了建立新的环境而摧毁旧的既有新环境。”
发展所需的第一件事就是创造需求,而创造需求的第一步就是制造不满。必须要让人们不满于他们所拥有的。这也就是说,发展是一场本土战争,人们自己制造,自行控制这场战争,使自己依附这台发展的机器。但是,为了让他们有能力购买这些产品,他们首先需要卖掉一些东西,那就是他们的劳动力。
从一开始,只有国家可以为了建立新的环境而摧毁旧的既有环境。这就是让·巴蒂斯特·科尔伯特 ( Jean-Baptiste Colbert ) 通过强制建立工厂来达到的,人们将作为奴隶工作。当列宁和斯大林开始发展俄罗斯的时候他们用机器粗暴的手段破坏了他们的日常去服从资本主义纪律。这个发展是指资本主义的发展。它并不是市场自发产生的,市场可以与传统社会毫无问题地共存。市场在非洲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希罗多德就曾谈论过它,这个市场没有创造发展。发展是一种权力寻求的企业,这是处于军事目的,只能通过国家行为来实现。
经济发展的基本固有矛盾是什么?
发展是增长的质变。发展是不息的,增长是无尽的。无限的发展与有限的地球并不相容。我们发现这种矛盾实在是太晚了。按照卡尔·马克思 ( Karl Marx ) 的观点:这什么都不算,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对劳动的剥削,这造成了阶级的对立。
“ 环境的限制和生态的挑战产生了矛盾,这创造了问题并摧毁我们系统本就站不住脚的基础。”
尽管这个矛盾日益显现,愈发真切。但仅仅威胁到这个体系是不够的,因为这个体系具有整合和操纵工人阶级的非凡能力。一方面,马克思极大程度地低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观念殖民。它通过系统的力量来破坏社会联系使社会分散。在这个层面上玛格丽特·特切彻 ( Margaret Tchatcher ) 说的很对。她说这不是所谓的公司,而是由跨国财团,这些财团拥有强大的媒体力量,具有操纵“社会原子”的能力,以维持现有秩序的存续。
幸运的是,这种操作并不总是奏效,在一个软极权国家如法国,是一种通过媒体控制的极权主义,当然苏联和纳粹的极权主义也是如此,这其中总是存在着分裂。这是发展的第二个矛盾,但我们不能清楚地看见它,这不是一个充分条件。目前环境的限制和生态的挑战产生的这个矛盾,这挑战似乎是法国体系不可持续基础的矛盾。
您所说的“分裂”,准确地讲它是从何而来?一些已经忍受“发展”影响的个人以及一些团体,还是那些不受影响的部分呢?
两者都有,我们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经验。自从1949年1月1号新萨帕塔主义者 ( néo – zapatistes ) 到达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 ( San Cristóbal de las Casas ) 解放了五个被叫做卡拉科尔( Caracoles )的区域。这种经验一直持续到今天,热罗姆·巴谢 ( JérômeBaschet ) 充分的记录了此事。我们还能看到两次厄瓜多尔革命和玻利维亚“ buen vivir(好好活)”信条显示出的尚未完全消失的原住民的复兴和抵御能力。
“ 必要明白的是,发展只是18世纪形成的发展意识形态在经济上的转译。”
与此同时,一个客观联盟存在着。它是由最先进的持有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组成,他们组织社会运动以反对发展。这场运动在墨西哥形成绝非巧合,因为在圣克里斯托瓦尔 ( San Cristуbal )有伊万·伊利希 ( Ivan Illich ) 的地球大学 ( l’Université de la Terre ) 。副指挥官马科斯 ( Marcos )是伊万·伊利希的学生。
必须要说的是,从这种实践经历中培养的理论思维非常重要。这场技术经济巨型机器和人民之间的斗争中,需要智力支持。 在西方,我们保持着一种分裂,那些反对”大规模不必要的增加苛捐杂税的项目”的人,就像养蜂人反对盐碱杀虫剂。比如:圣母院机场( L’aéroport de Notre-Dame-des Landes ),苏萨谷的里昂-都灵高速线( la ligne а grande vitesse Lyon-Turin dans le val de Suse)。或者是一些反对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战斗有很多种形式。搏斗不会缺席,它会来自四面八方。

从历史上看,发展概念在西方以外以其他形式存在吗?
我认为没有。这是一个西方的概念。我刚开始职业生涯的时侯,是发展的专家。当面对的是那些不了解什么是发展的人时,专家们的首要任务是设法找到翻译这一概念的词语。有时需要通过使用各种与它无关的词来完成。“ 对非洲中部富拉尼人( Les peuls ) 来说,以及对于几乎每一个族裔来说,发展就是要有更好社会关系。对西方来说这意味着拥有汽车、洗衣机、冰箱等。”
“ 对非洲中部富拉尼人( Les peuls ) 来说,以及对于几乎每一个族裔来说,发展就是要有更好社会关系。对西方来说这意味着拥有汽车、洗衣机、冰箱等。”
例如,我们翻译”发展”一词给富拉尼人,翻作”班塔雷 ( bantaare )“。这个词意味着”很好的在一起”。通过插画的形式,富拉尼人给出了他们建造房屋的图画。他们的房子有一个方形的基地,和中式箬笠 ( Chapeau chinois ) 的房顶。他们分别建造,然后在地基上组装。在这个重要的建设时刻,全村人聚集在一起妥善地安置屋顶。换句话说房子的完工需要和谐。整个村庄的联盟和村庄的团结奠定了屋顶。对他们来说班塔雷说明了在一起的想法,这与我们所谓的发展无关。对于富拉尼人和其他族裔来说,发展就是建立更好的社会关系。对西方来说,这意味着拥有汽车、洗衣机、冰箱等。
我们必须明白,发展只是扩张思想在经济上的转译。这种意识形态在18世纪长成,尽管早在12世纪,弗朗西斯·培根 ( Francis Bacon ) 的先人罗杰·培根 ( Roger Bacon ) 就发现了萌芽。意识形态首先涉及时间的表示。特别是在非洲社会,未来是一件未知的事情。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将面临的是过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的目标是回到过去,即祖先的世界。今天的穆斯林也是如此,他们想找到穆罕默德和他的同伴们当时的社会。这与扩张无关,这是一个嗜古者的看法,是一种逆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其中有很多优秀的观念。
其中的一些族群认为,发展是没有意义的。更何况对于许多这些人来说自然是神圣的。我的朋友雅克·戈德布特( Jacques Godbout )对与加拿大政府试图利用、开发以及向因纽特人提供资源有一些很好的文章。因纽特人家里拥有有太多的驯鹿,因此他们开始为这些动物开发加工厂。戈德布特回忆说:当政府派使节推动这个项目时,一位因纽特人酋长说道:“你知道,我们当然吃驯鹿。但我们和他们有很长的历史。”他问道:“我不知道我们能否这样对他们”。
“ 对于非洲社会来说未来是个未知数。他们认为那是已经发生过的事。那么在这个层面上,社会的目标是加入过去,也就是加入祖先的世界。”
哥伦比亚印第安人每年都会与鲑鱼进行放归仪式。当鱼类逆流而上,他们只捕捞所需的食物,他们将鲑鱼当成与他们一样的人类。他们举行隆重的仪式并将所有剩下的鲑鱼都放回海里,以便他们可以在第二年何以洄游。当白人来到那里看到大量鲑鱼时,他们建立了鲑鱼罐头工厂。河里很快便不再有鲑鱼了。美洲原住民对此非常反感,对白人不尊重这一惯例感到愤怒。也就是说无论是非洲中西部原住民,还是美洲印第安人或其他国家,都没有与我们的所谓发展相对应的观念殖民,正是这种观念支撑起了拓殖的家乡。也就是说,商品化和全面工业化构成了我们今天的生活。
非洲人类学家让·皮埃尔(Jean-Pierre Olivier de Sardan )在2017年3月的一次“伟大对话”中说:“一直以来西方的所谓发展都被尖锐地批评为西方帝国主义。三十年间拉图什( Latouche ) 对发展所做的一切,让他的名字意味着非常典型的批评态度”。您怎么看?在您看来发展具有不好的本质吗?
是的,因为发展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坚持人对人的剥削和对自然的榨取。这破坏了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一种全面的异化。如果我们能够给事物下定义为“邪恶的”,那我大概会说“发展是邪恶的”。
“ 发展是邪恶的。”
当然,发展的天真表述,让他被视作穷人的福祉。这使得我们去评论:这是一个“发达的”或是一个“欠发达的”。这是一个纯粹的意识形态观点。这是没有理论基础的为发展赋予意义。

您怎么看那些假设“科学”和“技术进步”能够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技术解决主义者”?
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可笑的小玩意,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益处且不重要。 当然这些东西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保护生态多样性。正如1970年代捷克环境部长表明的那样:当你的浴室里发生水灾,拖把确实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如果你还没有关闭水龙头或堵上漏水点,拖把起到的作用就没有多大了。因此“可持续发展”、“绿色增长” 、“社会团结经济”等概念都只是拖把。当今的挑战是正视这些问题,直面发展的本质,以及经济增长的方向。
具体来说,我们在正视眼前问题的最合适方式上存在一些争论。一些人主张改变个人行为,另一些人呼吁进行彻底的体制和结构变革,在这两种人之间存在着一些对抗。在您看来什么是我们需要去做的。
就我们而言我们已经选择“逆增长”。因为我们辨清了发展型社会问题的根源,也就是我们在其中放入的“无限性”,这也是现代精神错乱的核心思想。经济实际上是它的核心。无限化有它自己的三部曲。首先,生产的无限化带来了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被无限破坏。其次消费的无限导向了无限的需求制造,它为我们带来了人造的生活。结果是无论你是否想要,无限的破坏和污染都产生了。这就是我们所做的。
“ 几乎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都站在逆增长的一边,几乎所有的伟大哲学家和古代先贤都谴责了过度的危害。”
但是从我们只能用道德去限制这种无限性的那一刻起,用伯纳德·曼德维尔 ( Bernard Mandeville ) 的话来讲就是:个人的恶习造就了公共的美德。这是律法和先知。是资本主义,就注定是邪恶的。这不是浪漫的道德判断。它是邪恶的,因为这是人类的自杀。
在这种现状下,哪种哲学或是个人智慧需要在我们的个人和集体生活中被回复? 一个新的“伟大转场”是否必要?
一个转场,我想是的。几年来我在《乘客克兰德斯汀》杂志上推出了《逆增长的先行者》系列。我们已经用法语出版了二十多本书,用意大利语出版了15本。“逆增长”这个想法有两个主要来源,伊万·伊利希 ( Ivan Illich ) 是其中之一,我认为他是我的东家;科尼利厄斯·卡斯托里亚迪斯 ( Cornelius Castoriadis ) 是另一个。伊万 ( Ivan Illich ) 和利奥波德·科尔 ( Léopold Kohr )有所联系,利奥波德由与恩斯特·舒马赫 ( Ernst Schumacher ) 和埃里希·罗姆 ( Erich Fromm )有关。一点点的“逆增长”的想法在我脑海中扩大,然后我意识到了,从数量层面看,几乎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除了一些持有拓殖观念的和主张演进的理论家,都站在“逆发展”的一边。但是,这些在思想史上是一些小小的插曲,增长的历史也将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小小插曲。
事实上,所有伟大的哲学已经预见到了过度的危险;这是一些祖先的智慧,无论是亚洲人、印度人、中国人的智慧,还是非洲和美国的原住民。他们这些古老的哲学家,无论是伊壁鸠鲁 ( Épicure ), 第欧根尼 ( Diogène ) 还是斯多葛主义者 ( Les Stoïciens ) 都谴责了过度的危险!我们必须恢复这些智慧以避免我们过度,而经济的合理性恰恰是过度的。明确的说:永远要求更多得过分。